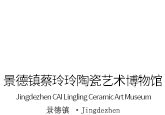家羚说瓷:陶瓷的地域性
2025-10-16蔡玲玲谈陶瓷#18
陶瓷的地域性体现在不同地区因独特的自然原料、工艺传统和审美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技术体系。

陶瓷的地域性,只要纵观历史上各地窑口的出现发展历程,就不难理解这一属性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不同地区的土质、水源、气候以及人文传统,共同塑造了陶瓷艺术丰富而鲜明的地方特色。尽管当陶瓷发展到了宋、明、清时期,景德镇在制瓷行业的地位不可取代,并集中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优势资源。但是整个陶瓷发展的历史,依旧由不同地区、不同窑口所共同书写。

定窑白釉刻“徐六铭记”铭皮囊壶(故宫博物馆)
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开始,陶器便依次在相隔甚远的多个文化中出现。甘肃秦安的大地湾文化陶器质朴粗犷,陕西宝鸡北首岭文化的陶器则体现出早期人类对器型的有意识塑造;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纹饰生动、色彩鲜明,展现了先民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致观察与艺术再现;山东宁阳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造型规整,胎体细腻,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陶器则以夹炭黑陶为特色,器表多饰绳纹,体现出南方水乡地域的独特风貌。

黑陶双耳小罐(故宫博物馆)
此外,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线条流畅,四川巫山大溪文化的陶器富于地域装饰风格,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文化陶器多为红陶,并常见鼎、豆等器形,河南陕县的庙底沟文化陶器在仰韶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纹饰更为抽象化与符号化,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黑陶薄胎光亮、器形优雅,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成就,湖北应变山的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简洁明快,甘肃广河的齐家文化陶器则多见双耳罐等器形,山东章丘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堪称史前制陶技艺的巅峰,青海的卡约文化陶器则带有浓郁的西北草原民族特色。
这些早期陶器几乎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陶瓷艺术地域分异的历史。

越窑青釉双系执壶(故宫博物馆)
而当瓷器出现之后,各个窑口开始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唐朝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北方邢窑的白瓷类银似雪,南方越窑的青瓷如冰似玉,形成“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越窑的秘色瓷更是以其莹润的釉色和精湛的工艺成为贡御珍品。此外,洪州窑、寿州窑、耀州窑、长沙窑、巩县窑等也都各具特色,如长沙窑开创釉下彩绘先河,耀州窑刻花青瓷刀法犀利、纹样生动。这种遍地开花的形式,不仅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与审美需求,也为此后宋朝瓷器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艺术与市场基础。

长沙窑花鸟纹壶(故宫博物馆)
在陆羽所著的《茶经》之中,关于“器”这一节,细致地分析了各窑口所产瓷器在茶事中的表现,其评价标准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趣味与实用考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这段经典论述,不仅是对茶具功能的品评,更是对不同地域陶瓷美学特质的精妙概括,凸显了陶瓷产品因其材质、釉色、造型的差异而在使用体验与艺术感受上呈现出的鲜明地域性。


此后的宋、元、明、清诸代,陶瓷发展依旧延续了各个窑口齐头并进的态势,只不过景德镇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质瓷土资源、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不断创新的制瓷技艺,以及在朝代更迭中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逐渐在众多窑口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宋代钧窑的窑变万千,汝窑的天青温润,哥窑的金丝铁线,定窑的刻花白瓷,耀州窑的犀利刻花,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建窑的兔毫油滴,吉州窑的剪纸贴花,无不展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与很高的艺术成就。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兴起,与景德镇的工艺创新密不可分,但也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因素。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设立更是将官窑瓷器推向高处,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品种层出不穷,但其背后,仍可见到如龙泉青瓷、德化白瓷、宜兴紫砂、石湾陶塑等地方窑口依据自身传统与资源禀赋,持续发展,形成了与景德镇并立或互补的产业格局,满足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

建窑黑釉兔毫纹盏(故宫博物馆)
纵观中国陶瓷史,不同窑口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兴起、昌盛、衰落的生命周期,但正是这种此起彼伏、各擅胜场的动态过程,构成了陶瓷历史波澜壮阔的主旋律。陶瓷的地域性,不仅是其物质形态的自然烙印,更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审美观念、生活方式与技术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多样性、包容性与创造力的生动见证。

长沙窑花鸟纹壶(故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