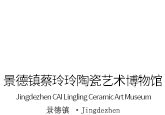清代五彩瓷的承袭与风格
2025-07-31蔡玲玲谈古彩#14
宫廷意志、官窑制度、欧洲贸易与市民审美多重力量碰撞后的又一次跃迁

清代五彩的嬗变,是明代五彩技术与审美积淀的必然延伸,也是宫廷意志、官窑制度、欧洲贸易与市民审美多重力量碰撞后的又一次跃迁。

清道光五彩婴戏图套杯(故宫博物院)
顺治八年,清廷始命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御器厂在明代旧址上恢复生产。旧制“匠籍永充”逐渐松动,出现“官搭民烧”之例,民窑得以参与御用器烧造。此时胎釉仍带明末遗韵,青花作主调,矾红、娇黄、水绿依序铺陈,雉鸡牡丹与洞石花卉疏朗而略带荒寒。民间画工因青花料短缺,偶以低温蓝彩补位,为康熙御窑“以蓝易青”埋下伏笔。

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觚(故宫博物院)
康熙朝前期,臧应选奉旨驻厂,御窑制度重回严整,而五彩也迎来了它高光时刻。工匠在反复试火后发现,以钴料研至很细,敷于釉面再经低温复烧,可呈一种沉静浓艳的宝蓝,远胜青花的一成不变;珠明料含铁很高,竟可烧出光亮如漆的黑彩,毫发可鉴;更以金箔熔入铅釉,赤金闪烁,历久不黯。三彩既备,五彩遂彻底摆脱釉下青花,一跃而为纯釉上彩绘。高岭土淘洗之精与二元配方之稳,使胎薄如纸、声清如磬,色层得以层层堆叠而不龟裂。刘廷玑《在园杂志》记郎廷极督陶事时称:“其写生之笔,渲染之妙,虽丹青家不能及也。”正是对此“生动之意”的由衷赞叹。

清康熙成化款五彩婴戏图碗(故宫博物院)
雍正帝性耽静穆,尤喜宋瓷之澹泊,五彩的喧腾遂被粉彩的柔腻渐次稀释。年希尧、唐英督理御窑,矾红让位于胭脂,翠绿易为水绿,金彩敛迹,黑彩仅留一线勾勒。题材亦由康熙的刀马人物、耕织图转为折枝小景、四爱图,诗书画印同器,留白处俨然倪瓒之疏林远岫。雍正一朝的审美转向却由传世实物与唐英《陶成纪事》的记录中可见:御器“仿古采今,以淡雅为宗”,五彩在此氛围中自然收敛锋芒,也为乾隆的再度张扬积蓄了回旋之力。

清五彩团龙宝相花纹碗(故宫博物院)
在乾隆朝六十年的时间里,档案中“五彩”条目骤增,却呈现两极:一端是奉敕仿明宣德、成化的青花五彩,保留铁锈斑、橘皮纹,以示溯源;另一端则大胆引入西洋透视与洛可可涡卷,创为“洋彩五彩”。乾隆时期的五彩瓷制作工艺精湛,胎体细腻,釉面光滑,色彩鲜艳且持久。在绘画风格上更加注重细节和色彩的层次感,线条流畅,图案饱满。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在五彩瓷中得到了比较鲜明的体现,唐英档册中屡见“器皿以备赏赉”之载,五彩至此已不仅是宫廷雅玩,更成为世界贸易网络里精品。与此同时,民窑趁海禁松弛,大量烧制克拉克瓷与纹章瓷,五彩的技艺随之流向世界,在欧洲早期工业设计的釉下蓝彩与锡釉之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东方基因。

清乾隆五彩瑞兽图瓜棱执壶(故宫博物院)
嘉道以降,御窑经费日绌,五彩命脉遂由官窑转入民窑。嘉窑尚循康熙旧法,惜料减工,蓝彩薄而泛灰,红绿亦失之黯淡;道窑器形厚重,缠枝莲与“喜”字开光满密而少层次,惟胎骨坚致尚能守成。同光年间,洋装订单激增,五彩与粉彩同炉并烧,出现“五彩加粉”的杂糅:人物衣褶先以黑彩勾线,再以粉彩渲染肌肤,背景山石则用康熙遗法堆蓝点绿,远观绚丽近看驳杂,《陶雅》叹曰“花堆五色,而神气散矣”。然民间青花五彩又别开一路,釉下青花写枝叶,釉上填矾红、水绿、赭黄,青红相映,朴拙中见鲜活,成为清末外销南洋的“客货”大宗。至此,五彩虽不复康乾之盛,却在民窑中延续血脉。

清嘉庆款矾红地五彩婴戏图碗(故宫博物院)
若从矿物与火候细究,清代五彩仍循铜、铁、钴、锰的旧谱,却在研磨与配比上更为精审:钴蓝经二次复烧可呈三至四层色阶;黑彩以珠明料加铅粉,光亮如镜;金彩借金箔熔融,永不剥落。乾隆《陶成纪事》把五彩与粉彩、珐琅彩并列,成为清代三大彩系之一。

清五彩加金鹭莲纹尊(故宫博物院)
纵观有清一代,五彩在制度松紧与市场呼吸之间先盛后散,却始终未绝,其技其韵,化作后世彩瓷的底色,亦成为世界记忆中的中国亮色。

清五彩开光博古花鸟图缸(故宫博物院)